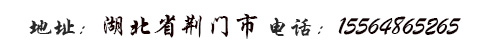我不羞于表达的感情我们这一年
|
补骨脂注射液零售价你了解多少 https://m-mip.39.net/baidianfeng/mipso_4325347.html 这个时代已经很难有你为之献身的时刻,你所需要做的就是,强壮体魄,然后一直在场,一直记录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图 本刊记者杨楠 编辑 杨静茹 全文约字,细读大约需要16分钟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刚知道母校历史系的一位教授退休了。也就是说,我去年下半年旁听的“中西文化交流史”是这位教授最后一次授课。这课我七年前旁听过,六年前选过又退了。原因是教授要求必须通过一个考试才能写期末论文,如果考试不合格,直接挂科。考什么呢?就考他每堂课时不时说的“这是一个简单明确的史实”,全是容不得弄虚作假的知识点。若是你笔记没记全,或是没背牢,必然挂科。而我生性懒散,不敢面对考试。 十二月的几堂课,我没去听,大多是年末忙工作。现在想起来真是懊悔万分,不知道教授有没有在最后几堂课说些特别的。课程内容我能记七年,稿子我可能只能记七个月。 我问同事琳玲姐,你最近几个月都没写稿子,你在干啥。她说看书,写点历史摘记。这两年我最喜欢的稿子之一就是琳玲姐的《光绪之死》(点击阅读),举重若轻,丝丝入扣。我的同学们大多读过此文,当我说我去《南方人物周刊》工作的时候,好几个立刻问:是写《光绪之死》的杂志吗? 想起来去年七月,和学姐在上海淮海路上散步,坐在一块亮眼的落地玻璃前聊天、喝汽水。她是个青年作家,她说有人和她说,喜欢她是因为她这个人,而非真的读过她的作品。她愈发明确,要保护个体的独立性,比如尽量不出席公开活动。她一直以来都觉得,她这个人,要比她的作品更重要。 在芒市 年一月 我和柴老师吃了个饭,算是认识了。他44岁,在同报系的《南方周末》写了十六年社会报道。他是山东人,身形高大敦实,不笑的时候有些苦相,笑起来又有些腼腆。 柴老师身上有种不合时宜的质朴,丝毫没有中年男性那种喜欢指点江山的油腻。他在饭局里看起来格格不入,不起哄不喝酒,好像显得过于固执,与他工作时的状态如出一辙。他们的编辑阿朱说,这行太苦了,没点固执撑不下去。 过去一年里,柴老师经常问我,你觉得这个选题怎么样,你觉得稿子这样写行么。我是后辈,并不想班门弄斧显得自己狂妄自大,往往先是一通赞美。但架不住柴老师连续追问,隔着手机屏幕都能感觉到他钻研业务的诚恳,不由得收敛起自己的场面话,认真讨论,好的坏的都要说。 有段时间我看柴老师的朋友圈,常常发现“社会新闻的‘反转’,会印证他最初的判断。我问柴老师为什么有如是推测,他往往是说事出反常必有妖,你要相信朴素的逻辑推断。去年十月他写了南京一家五人出游一人生还的报道,指出这家人曾经先后加入东方闪电教和新教。就这一点信息增量,他在南京待了二十天,找人找人找人,唠嗑唠嗑唠嗑,然后问到了。 今年年初回报系开会,柴老师领了《南方周末》的年度新闻奖一等奖,因为那篇全网二十亿次传播量的《“不寒而栗”的爱情:北大自杀女生的聊天记录》。他领奖时简单说了几句感言,说自己第一次拿年度新闻是年,第二次是年(唐慧案);他当时说,要用七年再拿一个,领导同他说,我看你用不了七年,柴老师说,领导你不知道,对《南方周末》的记者来说,拿这个奖有多难。没多久,他就因为几篇医疗报道被陷入了纠纷。那是他最低谷的时候,甚至觉得自己做不了记者了。但好在熬过来了,在七年快到了的时候,又拿到了。 他说得十分平静,没有任何细节描述,而我们在下面听得掉眼泪。可能我还是年轻,所以听到时间给人的灾祸和礼物被这样轻描淡写地说出来,心生钦佩。我们都尊重柴老师,但都没有勇气去过柴老师那样的人生,熬过种种。 二月 学校开学了。不出差的时候,我尽量回母校听课。 课总是常听常新。而毕业后听课,常能感觉到,老师们在“卫道”。他们用三节课和学生们说法国大革命中的偶然性,强调胜利者对历史书写的霸权;他们用一学期讲古代中外关系与疆域变迁,提醒学生们如今惯常思维的由来;他们讲宋代朝堂,讲历史上凡是被否定的事往往如此,史料记载了许多人曾为阻止其恶化付出努力,但就是不说“元凶”是谁;还有马哲原著精读,讲到现代社会最极致的,是创造者和被遗弃者的意义不均。一旦被遗弃,生命就已经结束,这比新教徒的焦虑更残酷。 有一回出差回来,听《理想国》精读,看到教授在讲台上潇洒地串联历史上的哲人。突然如释重负,课堂将我从每一个细碎的事实中抽离。吾生须臾,而沧海无穷,有什么可心急如焚的呢? 我讨厌所有大惊小怪的稿子,讨厌告诉年轻人应该怎样生活,讨厌传播焦虑。去年写了一篇裸辞口述,又写了一篇顾湘,今年可能还会写这样的故事。 朋友老康说你这顾湘写得就是个软文,你得写出她为什么要住得很远,她肯定有她的痛苦,选择背后有艰难。我觉得老康说得有理,但我觉得分歧本质还是老康他们这些北漂不相信人真的可以绕道而行,柔性抵抗,去过自己的生活。顾湘真的是因为城里房租高,面积小,所以搬去了乡下,你咋就不信呢? 别人说顾湘像梭罗,顾湘说不,她不想像梭罗那样说人应该如何生活。“别人怎样过都可以,我这样过就行了。” 在重庆,为了多和采访对象聊一会儿,给买菜再做菜 五月 第一次跑突发,和同行小汤遇到。为了躲避不明阻力,小汤抢发了一个快稿。发完他特别难受,觉得哪哪儿都不好(显然不是这样)。而后他就陪着我采访,同他《南方周末》的编辑说,他觉得自己做得不好,现在就想帮杨楠写一篇好点的报道。 当然我也没写好。只是我差不多要开始写的时候,他转去了另一个城市,继续突破之前一些守口如瓶的采访对象,想再写一篇。过了两天,他凌晨发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zhouzx.com/hzjy/11592.html
- 上一篇文章: 吃货看这里化州年例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