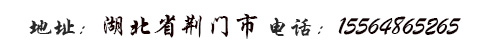被隔离的日子
|
被隔离的日子 一名美国医生奔赴西非,协助对抗埃博拉,在那里他不当心被一个针头刺了一下,两天以后,他开始发热。 自此,他的埃博拉隔离病房生活开始。在这段日子里,鲁宾逊看到了两个世界,两种现实。 在塞拉利昂一个埃博拉病区,刘易斯·鲁宾逊(LewisRubinson)偶然被针头刺了一下。几天后,他的体温逼近40度。 伴随高烧而来的是头痛、恶心和肌肉酸痛。到达位于美国贝塞斯达市的国家健康研究所(NIH)后不久,他又开始剧烈发抖,医生称之为“寒战”。 鲁宾逊自我安慰说,发热不太可能是由埃博拉引发。在被隔离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只能对自己说这些话。他身上没有出现埃博拉病人身上常见的皮疹,也没出现另外一个共同症状:眼白有血丝。不过,每次委曲从床上爬起来去洗手间时,他都要对着镜子检查一下。 一名医生朋友在中说,他绝不可能是染上了埃博拉,时间不对———高烧来得太快,寒战可能是身体对他服用的实验性药物的反应。 但是,身为马里兰休克创伤中心重症监护区负责人,鲁宾逊刚刚作为世界卫生组织(WHO)派出的专家,在塞拉利昂的凯内马政府医院工作了3周,他深知发热是病人感染埃博拉后表现出的首个症状。现在,全副武装的医护人员对他进行严格“监控”,对他的病情发展之快感到惊讶。那个针头可以为病毒进入他体内提供极佳路径,而且鲁宾逊暗自思忖,即便不是那个针头惹的祸,但或许在那之前,他已不知不觉被感染? 当体温不断爬升,大脑就开始纠结。现在,没人能判定他到底是一名出现药物反应的医生,还是一名埃博拉病人。 为难的毛病 在凯内马政府医院,穿着厚重防护服的医务人员闷热难当,最多只能在埃博拉隔离区待上90分钟到2小时。正因为此,那天鲁宾逊加快了工作速度,用手挤着塑料吊瓶,让里面的液体更快流到饱受折磨的病人体内。就在那时,他注意到了那个针头———留在1名年轻女病人床头的吊瓶内。他将针头拔出来,心想竟然有人不知道将针头这样留着是多么危险。他拿着针头走了大约50步,想到病房对面把它扔掉。但是,放置尖锐物的垃圾箱满了,因而他又把针头拿了回来。就在此时,针尖戳到了他的肉里。隔着两层医用手套,他能感觉到血在渐渐渗出。 他觉得自己太愚昧,同时觉得有点为难:在就要结束任务、带着团队打道回府、离开凯内马的前一天,竟然犯下这类毛病。同时,他不可抑制地感到一阵恐慌。 鲁宾逊迅速用消毒液清洗了双手,向同伴说明情况,让对方接班,而他本人则离开隔离区,在消毒喷雾中把一层层防护服剥下来。每天他都要一次次履行这套严格的15分钟消毒程序:脱下外层手套、罩衫(将受污染的那边折向里面)、然后是头套。消毒,消毒,再消毒。然后脱下工装库、面罩、护目镜。再来一道消毒。最后,终究脱下内层手套。 鲁宾逊看到血浸满了左拇指和部份手掌。他肯定自己的手套已受污染,针头刺得很深。这不是好事。 他步行去到医院附近一个临时办公室,给驻守在日内瓦的WHO风险战略师打。通话延续了25秒,然后断了。他再拨一次,这次说了大概15秒。通话只能听清大概三分之一。他转来转去,寻觅最好通讯位置,大概用了一个半小时,才解释完自己的遭受。 终究日内瓦那边做出决定:他要撤离。 别无选择。万一他感染了埃博拉,病情发作后再把他弄出去会比较困难。这很讽刺:已得病的非洲人不能出境医治,但是被针头刺伤的美国医生经过一通含糊不清的对话,便可以全速撤离。 那是9月26日,星期五。在塞拉利昂,WHO报告有2021例确诊、疑似和可能埃博拉病例,605人死于埃博拉。 在得克萨斯州,美国首例确认感染埃博拉的患者托马斯·埃里克·邓肯脱离了急救中心的抗生素医治,在未婚妻居住的公寓里开始隔离视察。 两难局面 埃博拉病毒的潜伏期是2到21天,症状一般在感染后8到10天出现。在去西非之前,鲁宾逊就知道凯内马政府医院已成为医务人员感染原点。近30名医务工作者被感染,很多死去,愿意代替他们位置的人很少。鲁宾逊正是被派去代替另外一名遭到感染的外国领队。 9月10日,当鲁宾逊带领着一支由近10位WHO专家和当地医务人员组成的工作团队到达凯内马政府医院时,发现这家以研究另外一种病毒性出血热Lassa闻名的医院正在埃博拉的进逼下不堪重负。 他们面对着两难局面:如果专心救治那23十位病情最重的患者,那末另外的八九十位怎么办?而且他确信,后者当中还包括一些没有感染埃博拉、但被困在此处没法离开、束手待毙的人。 关于隔离区内哪些是确诊、疑似和康复病例,工作队能得到的信息有限。这样一来,哪怕只是轮番问些基本问题(叫甚么名字、在这住了多久、出现症状多久了),给每一个病人两分钟,就会耗掉两个小时,甚么有效的医治都做不成。 乃至连记录信息都成问题。在医院那栋残旧失修的一层建筑里,不能使用电子设备,由于里面电力不稳定,也没有无线络。而哪怕一片纸也不能带出隔离区,怕它们携带病毒。最后工作队想出了一个方法:把数据写在纸上,离开时让人用拍照把那些纸拍下来。 总之,有很多问题亟待解决,而做这些事却并不是医治病人,消耗了宝贵时间。 还有,那无数在医院外的等待帮助的病人怎么办?如果工作队超负荷接收病人,全部医治链条就会崩溃。你只能对许多患者说“不”,虽然心里知道他们无处可去。 奢华撤离 这么多患者束手待毙,医护人员在照顾他们的同时,又能如何周密地保护自己呢?而且,医护人员的生命更重要吗?从操作层面讲,确切是这样。但这样说仿佛又很怪。而当鲁宾逊一个偶然的忽视便将他推向世界最先进的医疗系统时,这看上去就更怪了。 在一通又一通断断续续的后,一个撤离计划构成:当天下午,1名WHO司机驱车把鲁宾逊送到塞拉利昂的首都弗里敦,让他在那里等候。位于美国亚特兰大的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DC)的医生会安排人把一种实验性药物通过飞机递送给他,而他也将乘同一架飞机回到华盛顿。 那种药物还历来没在人类身上用过。它的功用是避免曾暴露在埃博拉病毒眼前的人病发,但见不见效尚不清楚,由于它还没有经历美国食品与药物管理局(FDA)要求严苛的随机临床实验。 当一种新型疾病出现,或一种宿病突然又开始传播时,搜集一种药物的有效性数据是非常困难的。真实世界并不是《犯罪现场调查》,科学研究进展远远落后于病毒传播速度,所以新的药物和医治方法常常在没人知道是不是见效的情况下紧急投入使用。2003年非典疫情爆发后,鲁宾逊就曾见过这种情况;2009年猪流感蔓延期间,他曾帮助牵头进行美国政府的有用信息搜集行动,当时FDA授权将实验性抗病毒药物Peramivir临时用在一些住院病人身上,有1200人用了药,但采取的方式并不能提供关于该药有效性、安全性的确实数据。 所以,做出“服用实验药物”的决定对鲁宾逊来讲很容易,产生在他身上的一切将成为临床数据的一部分。这是他的事业———他是临床研究博士。只不过这一次与以往不同,他是在听诊器的另外一端、在试管内部体验这个进程。 决定撤离后,他与同事进行了30分钟使人懊丧的告别———离共同战役3周的火伴们一米远,只能拥抱空气。 那天晚上,WHO司机将他送到弗里敦。他选了一家最好的酒店过夜,那里似乎是埃博拉国际应对组织许多高级成员下榻的地方,设施不错,有淋浴、空调、无线络。他看到了新鲜水果和舞厅,人们在舞蹈。在相互接触。 弗里敦离凯内马只有大约300千米,但鲁宾逊感觉自己已身处另外一个世界。在凯内马,人人将“不接触”信条铭记在心,你的笔是你的笔,你的是你的,甚么都不能分享,不能借用,以避免沾染。 在飞往美国弗雷德里克的几近整12个小时里,鲁宾逊完全没有症状。他坐的是一架跟美国国务院签了合约的私人飞机,机上有三名飞行员和两名护士,配有一个隔离单元,鲁宾逊觉得自己暂不需要。但是,这架湾流GIIII飞机在马里兰州降落前大约10分钟,鲁宾逊开始有感冒的感觉,不太舒服,医生怀疑是新药起作用了。他爬进一套保护性装置内,内心模糊地意想到:现在这类措施是他人用来隔离他,避免被他感染的。飞机1降落,人们就迅速把他推上一辆救护车,送往NIH。 躺在密封的隔离担架里,鲁宾逊感觉依然不错。他透过车后窗看着眼前的超现实场景,仍觉得有几分可笑:两辆警车和1辆消防车跟在救护车后面,警灯闪烁,警笛长鸣。他不知道前方等待的将是什么,和这一切的本钱有多高,要花多少万美元。 他刚刚在非洲看到,人们———包括婴儿———静静死去,没有甚么钱花在他们身上。 9月28日,星期天,下午4点,鲁宾逊入住NIH。 与此同时,在得州,邓肯又被急救车送到了急诊室,开始隔离。两天后,CDC宣布他感染了埃博拉。 焦虑与现实 NIH的特别临床研究中心有七个床位,4年前开设,但其中只有两张床位能够满足“接待”埃博拉患者的条件。 入院以后,鲁宾逊开始发热,药物也没法减缓,并感到极度恶心。研究者极尽详细地记录他的种种身体反应和数据。一条塑料管通过他臂上一条静脉血管,通向心脏上方更粗的血管,每天为研究者提供血样,用于监控鲁宾逊的身体性能、他的免疫系统对药物的反应,和检测他是不是感染了埃博拉。每天四次,身着超现实主义风格防护服的护士出现在病房,收集各种数据,全力获得经验。鲁宾逊躺在一堆毯子下面,还是觉得冰冷。房间设定为19摄氏度的恒温。 两天以后,他的体温开始下落。又过了两天,烧退了。 10月1日,鲁宾逊已进入21天潜伏期的第5天。 在塞拉利昂,WHO宣布已发现2304例埃博拉病例,622人死亡。 在得州,当局开始追踪邓肯接触过的人,在他曾逗留的公寓里居住的四个人开始在家隔离。 鲁宾逊退烧让医生的耽忧有所减缓:明显这场高烧的罪魁不是埃博拉病毒,而是由新药引发。 但是美国民众的焦虑正在加重。 在隔离病房的电视上,鲁宾逊看到从没去过西非的主持人针对埃博拉发表长篇大论。一名所谓权威赞美那些正在研发中的医治手段———昂贵的新药可能有朝一日改变埃博拉疫情的面貌。而鲁宾逊想到的是,在目前这轮疫情中,愿意投到非洲人基本医疗卫生方面的钱是多么少。在凯内马,医护人员仍在使用陈腐的静脉注射装备。 电视上的专家反复强调,美国的医院已做好接收埃博拉病人的准备。怎样可能呢?鲁宾逊想。大约6000家医院都做好了准备?不错,那些医院可能具有辨认埃博拉病人、保证医护人员安全的能力。但他深知,医治埃博拉病人的专门知识和装备,和外围护理的本钱,超越了大部分美国医院的能力。在非洲,从那些具有多年对抗埃博拉经验的医生那里,他学到了宝贵的实践知识,从而了解到,哪怕美国那些高质量的大型医院,都不能在短期内迅速做好准备。应对埃博拉,要把注意力放在全部地区的医疗部署上,这比期待某家医院能够胜任所有工作更有意义。 他也不认为,媒体提供的那些简化信息可以打消人们的疑虑。面对埃博拉,美国需要更好的战略,在充分科研和实际经验的基础上拟定的战略。这才是公共健康部门要做的。 隔离生活 与此同时,鲁宾逊开始体会到,“隔离”其实不意味着“独自1人”。 他看不见护士站,但是通过摄像头,护士可以一天24小时视察他。透过一扇窗,他能看到1间接待室,工作人员正用消毒剂擦着地面,负责他的两名护士所穿的防护服比凯内马政府医院的防护服更加“全副武装”。在这里,他具有专人病房,两名护士为他服务,而在凯内马,两名医生要照料100多名病人。 他习惯了通话器传来的机械化的声音。 “你想好午饭吃甚么了吗?” “闻到消毒剂味道,你没问题吗?”固然没问题———有好几周的时间,他每天都要接受消毒剂喷雾的沐浴呢。 但是,既然他已退烧,没有症状了,为何还要继续住在这里?“住院隔离”是针对确诊病人的。 经过专业训练的重症病房和传染病科护士现在不得不适应一个健康人的需要。他们手写一张便签贴在了马桶盖上,提示他便后不要冲厕所,由于他的排泄物仍要用杀毒剂处理。 鲁宾逊得出的结论是,如果不是缺少控制,埃博拉疫情不会恶化到现在的样子。与西非的医院相比,他在NIH所住的这间病房条件完备,房间宽阔,有一张床、一张椅子和一个衣橱,医院发给他一个配有可消毒封套的iPad,嵌在墙上的电视屏幕是普通电脑的两倍大,他还可以用膝上键盘打字。 也许心里并没有幸存者的负罪感,但鲁宾逊急着回到“战场”上去。在西非,感染埃博拉的人每三周便翻一番,在美国,关于埃博拉的忧愁正在升级。相干信息不断变化,政策可能会被过时的想法和恐惧所左右,而不是听科学的指挥。与此同时,他,一名临床和应急经验丰富、并具有第一手埃博拉病例处理经验的医生,身心健康,却穿着病号服,无所事事地坐在隔离病房里。 10月3日,星期五,遭受针刺后一周,鲁宾逊感觉自己健康,精力充沛。 在塞拉利昂,WHO报告已发现2437起病例,623人死去。 在得州,邓肯仍在住院,到了周末,医院宣布他病情危重。 沉默是金 从新药影响中恢复第5天,检测显示鲁宾逊身上没有埃博拉病毒,而且从未感染过。一名朋友把他从隔离病房接出来。在明亮的秋日阳光中,他们驱车45英里,从贝塞斯达回到了鲁宾逊位于巴尔的摩的家,在那里他开始了为期10天的强制性在家隔离。 世治疗白癜风哪家医院好界从一条平淡非常的中得知了鲁宾逊离开NIH的消息。“今天早些时候,从塞拉利昂飞回美国并于9月28日入住NIH临床中心进行视察的病人,在高风险接触埃博拉病毒感染后,消除危险,回到家中。”在鲁宾逊本人的要求下,文中没有提及他的名字。 10月8日,星期三,鲁宾逊在自家床上醒来。这是一个月来第一次。 在塞拉利昂,WHO报告已发现2789例埃博拉患者,879人死去。 在得克萨斯州,托马斯·埃里克·邓肯死亡。 马里兰州对在家隔离的规定十分严格,鲁宾逊小心翼翼地遵照。4人获准可以看望他,给他带来食品。每天两次———上午9时和下午5时,一名医生会打过来,进行例行询问:有没有发热、头痛、腹痛、恶心、呕吐、腹泻或缘由不明的出血……?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没有症状,对他人没有构成风险。 在此期间,鲁宾逊继续研究应急战略,参加讨论,监控埃博拉疫情的发展。得知达拉斯两名护士由于医治托马斯·邓肯———美国唯一确诊患者———而感染埃博拉时,他感到悲痛,但是其实不意外。接收了一名病人,结果有两名医护人员感染———这个消息证实了他对美国预防和感染控制能力的担心。如果非洲每位病人都感染两位或更多医护人员的话,那末那里的医护人员现在都已死光了。 他曾亲眼看到病毒如何在非洲蔓延,占据上风,就儿童白癜风的原因像现在亲眼看着对埃博拉的恐惧开始在美国占据上风一样。正由于如此,整整21天里,这位医生守口如瓶,不向外界公布自己的遭受。在他能够利用科学,帮助人们在现实和头脑中积极对抗埃博拉之间,最好沉默是金,以避免引发恐慌。 10月17日,星期五,刘易斯·鲁宾逊的病毒潜伏期结束。 在塞拉利昂,WHO报告已确诊3410名病例,1200名死亡,并用“猖獗”来形容埃博拉的沾染速度。在那3410病例中,有40是他被隔离的21天里确认的。 在贝塞斯达,首位在美国境内感染埃博拉病毒的护士妮娜·范(NinaPham)头天深夜从达拉斯转移到了NIH,开始了自己的住院隔离生活。她是被邓肯沾染的两名护士之一,在鲁宾逊曾待过的特殊临床研究中心,她成为首位埃博拉病人。 原作:FrancesSteadSellers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zhouzx.com/hzzx/521.html
- 上一篇文章: 澳门富婆赠200万实为骗局女子共被骗23
- 下一篇文章: 贝克汉姆带小七现身洛杉矶街头小七大爱冰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