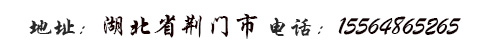古代方志传统杂记的方志编纂学功能与价
|
北京中科专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8%98%e4%ba%91%e6%b6%9b/21900249?fr=aladdin前言 章学诚曾指出“丛谈”的基本性质是“征材之所余”,可见这类门目在方志整体的文献编次与归类中,实际上发挥着很特殊的功能和意义,用以汇合与保存方志家对各类材料进行分门别类、筛汰裁剪之后的那些“剩余材料”。由此来看,“杂记”的设置,一方面能够保障方志体例的整严,同时又能确保各种琐碎的地方史料能得到保存。 《周易·系辞上》说:“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类聚”是古人很重要的编纂方法之一。中国古代史学从产生之初,就是以“区分类聚”作为重要的编纂思维,而方志编纂,同样是以文献搜集与整理、分类作为首要工作。 古代方志,往往分为众多门类,如光绪《通州直隶州志》就将内容分为12个大类,并于各大类下又细分若干子目,如“疆域志”包括沿革、星野、形胜、都里、市巷;“山川志”包括山、水、名迹;“建置志”则包括城隍、廨署、井泉、桥梁等。 然而,方志家在对地方文献进行分门别类的过程中,往往会发现有些材料难以归类,于是需要另立一个门类,来汇归这些“无类可附”的内容,那就是“杂记”。如民国《临晋县志·杂记》小序说:“人非一途,事非一致,无类可入,而又不可没者,则归诸‘杂记’,此编书之体例也。” 康熙《建宁府志》云:“篇末曰‘杂志’,归余于终之义也。”这样的“归余”意识,反映古代方志家不轻易割弃那些“无类可附”的剩余材料,而将之保存于卷末的一种“慎余”的文献学态度。那么,将“无所系属”的材料“归余于终”,对于方志编纂而言,有什么具体意义呢? 首先,将琐杂错出的材料从正志中抽离出来并另外归置,有利于维护正志本身整体的体例。如乾隆《潜山县志·凡例》云:“体不可紊,而事不可缺也,故综之以‘杂类’终焉。”光绪《东平州志·杂缀录》小序说:“别之为杂,正地志谨严之义尔。” 可见,志体之“谨严”与“不可紊”,实为方志家立“杂记”的一个主要目的。此外,明代田汝成作《西湖游览志》,又编《西湖游览志余》,《四库总目提要》曾指出其另编《志余》一书的意义:“盖有此余文,以消纳其冗碎,而后本书不病于芜杂,此其义例之善也。” 从具体的修志实践来看,当方志中有些类型的材料过于稀少,不足以单独立为一门,更不宜强附入他类时,归入“杂记”即为适当的方式,如光绪《重修华亭县志·凡例》说:“物产无多,故入‘杂志’。” 乾隆《颍上县志·例言》说:“寓贤及仙释、方伎,颍邑所见绝少,故不立门类,间有一二事可采者,附入‘摭遗’。”可见“杂记”能够容纳那些只有寥寥数则,难以专立一门的材料类型,从而避免了正志门目过于细碎的问题。 其次,则是通过将“次要”文献“贬入杂记”,来维护儒家正统史学的意识形态,借以表达方志编修者的学术立场与文献价值判断。如嘉靖《武康县志·杂传》小序说:“天下之事,行有纯、杂。杂也者,纯之别也。夫道,一而已矣,一则正,正则纯,于是有非道之正者,斯谓之杂矣。” 在这里,方志学家利用“纯”“杂”对举的方式来解释“杂”之义,并将“纯”归为“正”,“杂”遂为“非道之正者”,“杂传”于是成了方志学家辨别“正”“邪”的价值判断的产物。李义壮《三水县志序》也说:“君子之志于道也,不可不察夫邪、正之辨也,故次之以‘外志’。外也者,外之也。” 可见,方志家立“外志”一门的用意,也是要将他们价值观念中“非道之正”的文献内容排斥出去。具体的判断标准,包括几个不同的方面。第一,是出于政治教化的实用价值观念,而将缺乏政教功能的次要内容排除在外。 如康熙《陕西通志》说:“有益于政治者,详于正文。‘杂记’者,明堂之散才,大海之余波也。”即是以“杂记”来记载那些无益于政治的、对于地方治理来说缺乏实用性的边缘事物。又,乾隆《化州志》说:“古迹、丘墓,名不列于山川,义无关于田赋,不得不以事概之。” 由于古迹、丘墓这类地理空间缺乏实用性,该志遂将之归入“纪事”门。第二,是基于史学实录精神,将那些可疑性材料区别于正志之外。如康熙《增城县志·外志》小序说:“史志实事,一切虚渺不经者,悉外之。”因此许多出于稗官小说的名人轶事、神怪异闻等记载,都往往被归入“杂记”。 第三,是基于儒学本位的立场,将“异端邪说”色彩的内容区别出去。古代方志一般都立有“寺观”“仙释”一类门目,然而站在儒家立场,修志者对佛教、道教内容多持贬斥态度,如康熙《郴州总志·凡例》云:“九仙二佛,盛传郴土,与祥异、兵燹、寺观,俱不敢列正卷,以妖不胜德,乱不胜治,二氏何敢敌吾儒?故以‘志余’目之。” 贬黜二氏之意甚重,遂将“仙释”“寺观”都归入“志余”。另外,方志也多有“方技”门,记载医卜术数一类人物事迹,他们同样不以儒学之教为业,而主要从事占卜、行医等专门技术,因此同样多为儒者所轻。 如道光《东阿县志·杂记》小序说:“二氏之学,百工之事,儒者所不乐道。……他志多以仙释、方技列于人物,而‘丛谈’别为一门,试思仙释、方技果足当邑之人物乎?邑之人物,必以仙释、方技为重乎?怪者,圣人所不语也,仙释、方技,非圣人之道也,故统归之‘杂记’。” 可见“杂记”设立,有时也表达了方志学家对于儒学以外的“异端之学”的贬黜态度。第四,是从华夏文化中心立场,将不习于中原“文明声教”的少数民族等所谓“蛮夷”内容排斥到“杂记”中。如万历《漳州府志·杂志》小序说:“杂居徭人,异类之族也。” 因而将“徭人”之目归入“杂志”。康熙《增城县志》亦将“狪猺”归入“外志”,并指出:“彼徭獠之不知王法,与残民者之茂乱王章,孰非自外于天地哉?故外之。”由此来看,古代修志者立“杂记”以“归余于终”时,他们所谓“无类可附”“不应阑入他类”等说法的背后,有时并不只是单纯客观地依据文献性质来进行分类,而是存在着强烈的价值取向,意在将那些被贬斥的内容区别于“正志”之外。 因此,我们考察古代方志立“杂记”的观念与做法时,不能忽视其中的传统意识形态因素,在借鉴之余也要有所警惕,将那些带有旧时代思想印记的观念和做法剔除出去,去芜存菁。 方志“杂记”中的材料虽然是次要的、不合于正志之体的“征材之所余”,但它们依然具有保存下来的价值。关于“杂记”的价值,过去的学者在倡议新编方志应保留“杂记”一目时,已多有论及,如梁滨久认为方志设立“丛谈”可以“扩大志书内容含量,补充各部分记事之不足,起印证史实,深化内容的作用;可备谈资、增雅趣、长见识、益心身”,也能“增强地方志书的趣味性”。 宋世瑞则认为新修方志保留“丛谈”之目将有助于在方志中保存笔记小说文献,并“拓展了区域性的精神空间”“为方志这种史之别裁增添了更多文学意味”,且为后世保存口述文学研究的文献。任根珠亦认为“杂记”篇若在新方志编修中加以合理应用,则“志书的资料性、可读性、趣味性定会得到明显提升”。 这些说法已将“杂记”的主要价值概括清楚了,而笔者这里将结合古代方志家本身的论述,将“杂记”的价值分为史学的、文学的与地域文化的三个方面,对此问题进行理论史的梳理。首先是史学方面的价值。 在中国古代,方志一般被归入“史”的范畴,因此“杂记”作为方志中的一个门类,其首要价值自然也是在于史学,具体而言,就是要“补正史”“资考证”。如光绪《怀仁县新志》说:“杂志之设,所以拾遗补漏。……盖一邑之中,逸闻琐事、巷语街谈,虽近小说家言,亦足以备考镜、资谈故。” 虽然方志“杂记”中载录的许多都是地方上的街谈巷议、奇闻异事,但从古人的观点来看,这些材料就未必都是虚构不可信的,反而能够提供一种不同于正史视角的叙事,补充人们对于地方历史的理解。 至于那些看似荒诞不稽的故事,古人也并不废弃,如嘉庆《武义县志·杂记》小序说:“古人正史之外,有外纪、外传、杂录、杂记,其中虽多抵牾或诞谩无稽,然亦存而不废,所以广见闻也。”因此,面对真实性存在疑问的、难以征信的材料,“过而存之”“存而不废”才是较为妥当的态度,这样才能留待后人去进一步考订。 即使无法确认记载的真实与否,保留一个古人留下的叙事,无论如何也有增广见闻的意义。此外,许多神怪传说当中还寄寓了道德劝惩之意,史学可信度不高却有深刻的教化功能,如光宣《宜荆续志·杂志·纪异》小序就说:“神降于莘,石言于晋,于传有之,非以语怪,振聩发聋,使人猛省耳。” 又如道光《瑞金县志·杂志·记闻》的小序,亦明确不以可信度作为标准,而更重视这些故事“正俗”的作用:“虽偶有异诞而不背于经,庶足以信后,而为正俗之一助,用昭敬惧之意云尔。” 因此,方志“杂记”中的地方轶事异闻,不但能够拾遗补阙、增广见闻,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还是充满乡土气息的道德故事,因为和他们生活的地域息息相关,而能达到更好的教化效果。 |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huazhouzx.com/hzzx/13976.html
- 上一篇文章: 河北中药采购中药批发今日中药材产地快
- 下一篇文章: 没有了